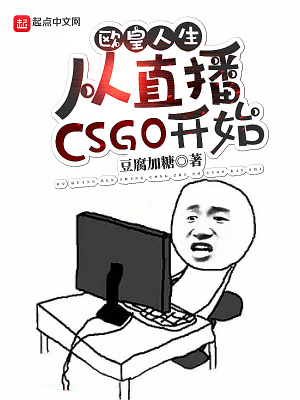夜读居>天幕:玩县令模拟器被围观了 > 13良田不产粮(第2页)
13良田不产粮(第2页)
他昨个睡得早,也睡得死,未曾真亲眼见着做夜发生的事儿。
可早上一起就听说的那场夜半捉拿张贵的凶险。
原先还不觉得有什么,如今一看李景安,脑子李瞬间有了画面。
忍不住暗自咋舌:这这这……张贵这群咋这么坏哩,给这么好的县太爷气成这个样子。
刘老实喉头滚动,笨拙又真心地开口:“大、大人,您…您身子还好吧?昨夜……可曾伤着?”
语气里是毫不作伪的关切。
家中的重担因李景安而卸下,如今他这满心满眼的,都是对这病弱恩人的担忧。
李景安微微牵起唇角,露出一抹虚弱的笑意。
他摆了摆手,声音微哑带咳:“无妨,老毛病了。说来也怪,自打这县里…嗯,事情顺了些,”
他含糊地带过“繁荣度”,咬字又清晰了一点:“这胸闷气短的毛病反倒轻了不少。虽还是容易乏,咳两声,倒不至于像先前那般喘不上气,憋得慌。”
话是这么说着,李景安的心中掠过一丝异样。
莫非那“繁荣度”还有滋养病体的功效?
李景安笑着谢过刘老实的关心,目光落在旁边沉默肃立的老者身上,脸朝旁微微一侧,目光透着询问。
刘老实这才如梦初醒,连忙躬身:“回大人,小的…小的和家里商量过了,厚着脸皮,想跟您借…借五吊钱。”
他紧张地搓着手,侧身引荐,“这位是小的族叔公,王家的族老,最是公正信义。”
“小的…小的请叔公来,做个见证,立个字据,心里也踏实。”
李景安,闻言目光结结实实的落在族老身上。
老人须发皆白,皱纹深刻,眼神却锐利清明。
他背脊挺得笔直,布满厚茧的大手垂在身侧,手指微微蜷缩,指甲缝里满是泥土的痕迹。
李景安心中了然,先是指着一旁简陋的椅子,温言道:“老人家请坐。”
又唤了一声,“木白,取五吊钱,还有笔墨纸砚来。”
很快,五吊沉甸甸的铜钱放在桌上,旁边是铺开的纸,磨好的墨。
李景安撑起身,靠坐在床头,接过笔,刷刷几下,一蹴而就。
但在递出去的时候,李景安的脸上闪过一丝明显的羞色。
他的字迹歪歪扭扭,像一群刚出壳,只知道乱爬的小蝌蚪。
许多笔画都有明显省简,横不平竖不直,族老侧头觑眼看了个,只能勉强能认个大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