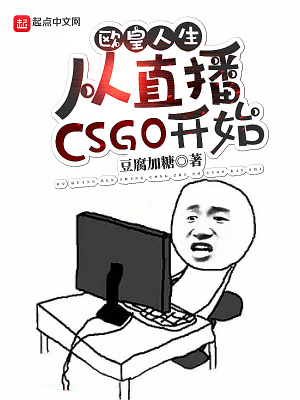夜读居>光渊昭溯之骆为昭的三十八岁 > 7第 7 章(第2页)
7第 7 章(第2页)
“裴溯、裴溯?”骆为昭轻轻拍了他的肩膀。
裴溯挣扎着清醒过来,眼神迷茫地在面前人的脸上扫过,右手撑起半个身子,眼看打着晃又要倒回去,骆为昭眼疾手快地扶着他。
“师……你……”
两个靠垫支着他坐起来,裴溯没来得及开口,很急地深吸一口气,他呼吸似乎到不了肺底,一口气没呼完又急促地喘了两声。
他此时握着骆为昭的手才能坐稳,双手撑着膝盖又要向前倒,额头抵着肩膀剧烈地喘息。
骆为昭几乎能感觉到薄汗顺着衬衫的布料淹入他的肩头,比世界上任意一种毒药更刮骨。他的嗓子被这一声声喘息勒紧,感觉浑身的血冲上了天灵盖,眼前一黑接着一黑,感应不到手脚。
他本能地、一遍一遍去拍眼前人的背,重复着名字。
直到裴溯一口气捋顺了,骆为昭才惊觉自己也能正常呼吸,膝盖一软,单膝跪地的支撑变成双膝跪地。
他想骂,也想问,从接电话到回家不过一个小时,你到底干嘛了?接着他灵光一现,突然意识到,裴溯平时也不怎么打电话找他。骆为昭哑着嗓子问,“不舒服怎么不直说?”
对方没有回答,大抵还是难受,额头埋在自己的胸口不出声。
骆为昭看不下去,转身就要扛起他,“走,去医院。”
裴溯缓过一阵,拉着他的手,摇头,“有点低血糖。”他垂着眼皮的时候神态无辜,乍一看相当值得信任。
骆为昭半信半疑,沉默地去给他冲了半杯糖盐混合的水,让他就着手,一点一点喝掉。
“真没事。”裴溯重复一遍。
骆为昭给他搀回半躺在沙发上的姿势,拉过沙发凳坐在他旁边,又从餐桌上把菜扒拉到大碗里,端着大碗坐在他面前边说边吃:“裴总,钱是赚不完的,你钱赚再多,买再多车子房子,这能住得过来吗?你那鞋得有四十多双了吧,下辈子变成蜈蚣都穿不过来。物质已经到了极大丰盛的阶段了,咱来点更高级的精神追求行不行?”
裴溯笑着说“嗯”,“可是师兄,我这是在追求高级艺术啊,为儿童服务呢。”
骆为昭一听知道他没往心底去。得,白说。
人看起来好一些了,有精力斗嘴了。骆为昭去餐桌上剥了几颗虾,拿干净的碗装下,拣着一口一口喂到裴溯嘴边,白牙一咬就吞下去,像喂猫一样。
猫张嘴等投喂,手机里打开了一部巴黎圣母院的电影在看,屏幕侧着,骆为昭也潜移默化地接受一些文化熏陶。
按照以往的经验,这大概也只是看起来吓人的小毛病,枪伤使他切除了一部分肺叶,胸闷和气促都是轻微表征,秋冬天会加重。
骆为昭洗完碗,坐在沙发边上又仔细观察他一段时间,直到手机里催促他的消息变得密集——陶泽去跨区参加经济案的抓捕不在sid,留守人员里只有他一个人有资格负责大案要案的签字。他站起身往大门口去,“那我去给提审收个尾巴,你今晚别洗澡,我回来给你擦。”
裴溯背着他举起手,比了个ok。
于是他仰天大笑出门去,万般悔恨回家来。事后骆为昭在病房外一遍一遍复盘这一整天的时候,恨不得跳起来扇当时的自己一个大耳光。
-
裴溯盘腿坐在床上审阅苗苗发过来的重新安排的项目建设排期。
工地上出了这么一件事,闹得人心惶惶,警戒线拦得住人看热闹,拦不住私底下的流言蜚语。一会儿说是本来人没死,是给开挖机的叶工掘断的;一会儿说是得罪了什么大人物,放出来杀鸡给猴看……传得那叫一个有鼻子有眼。
骆为昭进房间来,问:“怎么不睡?”
裴溯抬头,“睡多了”,他轻推镜框,“干会儿活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