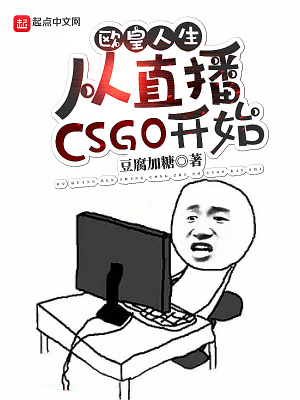夜读居>说了多少遍,踢球的时候要称职务 > 第一百一十三章 19岁的夏天(第6页)
第一百一十三章 19岁的夏天(第6页)
可公寓外,体育新闻正滚动播放他的进球集锦,报纸头条印着他被汗水浸透的侧脸,酒吧里的球迷举着啤酒争论他该去皇马还是曼联。
顶级银行的账户里静静躺着几笔八位数的转会预算,豪门的财务总监们早把欧元码得整整齐齐,只等罗伊的签字笔往合同上落下最后一划。
耐克、可口可乐和劳力士的市场部分别锁着门开小会。
现在三家公司各自闷头算账,虽然算法不同,但计算器最后跳出来的数字都长到让人眼花。
这个夏天,罗伊的每个小动作都像点石成金的魔法,让品牌方们数钱数到半夜笑醒。
与此同时,五六个国际品牌的精算师们正在连夜开会,把罗伊的曝光度、比赛收视率全都换算成欧元,精确计算着签下他能赚回多少利润。
此刻全球至少有七八架航班正飞往他所在的城市,头等舱里坐着不同品牌的谈判代表,每人的公文包里都装着厚厚一沓代言合同。
这些跨国公司的精英们,都是为了同一个19岁的年轻人专程飞来的。
而此刻的罗伊,正为乔伊那句“女人就像冰淇淋”笑到可乐从鼻子里呛出来。
次日,《队报》记者杜鲁克和罗伊约在巴黎蒙马特一家僻静的咖啡厅。
罗伊搅动着浓缩咖啡,侃侃而谈:
“那座奖杯不属于我,也不属于23名队员,它属于每个在街头踢易拉罐的法国孩子。金靴奖证明了一个来自小城市的小子能靠双脚改变命运,而最佳球员的意义在于,当移民的后代举起奖杯时,马赛和巴黎的郊区同时响起了欢呼声。”
“我的曾祖父是中国劳工,母亲是越南来的难民,他们教会我如何在夹缝中生存。但法国给了我机会,让我能站在世界面前,证明这片土地可以包容所有肤色和故事。当国歌响起时,没人问我祖上来自哪里,他们只看到我胸前的三色旗。”
“现在经过尼斯的中餐馆,还能看见老板把我的比赛照片贴在收银台旁边。那些华人孩子看着我的眼神,和当年我看着齐达内时一模一样,这就是足球最美好的传承。”
杜鲁克问起他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时刻。
罗伊沉默了片刻:“不是受伤,也不是输球。是捧起欧洲杯时,看台上找不到我父亲的身影。”
杜鲁克放下钢笔,录音笔的红光在沉默中持续闪烁。
“这是你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到他。”
“是的。”
罗伊轻轻转动着咖啡杯,“十一年了,我总在逃避这个话题。但最近我发现,越是刻意不去想,记忆反而越清晰。”
“你知道的,我来自滨海布洛涅。我父亲是个华裔移民,在我八岁那年永远留在了北海。”
“我父亲这辈子都在和海洋较劲。我祖父身体不好,那个叫玛利亚的法国意大利混血女人,我的祖母,抛下他们走了。他从水手做起,在渔船上干了半辈子,四十岁才攒够钱买下自己的渔船。你知道他给船取名叫什么吗?‘玛利亚号’。”
“我小时候不懂,问他为什么用抛弃他的人的名字命名自己的船。他叼着烟斗说:孩子,有些名字不是为了纪念,而是为了提醒——提醒自己永远别活成那种人。”
“我八岁那年冬天,‘玛利亚号’在北海遭遇风暴。船舱漏水时,附近的拖网渔船赶来救援。大部分船员都上了救生艇,但我父亲发现轮机长还被卡在底舱。他让大副带着其他人先走,自己转身去救人。”
“救援队说,他们最后看见我父亲时,他正用消防斧砸开变形的舱门。就在他拽出轮机长的瞬间,折断的主桅杆砸中了他们。轮机长被海浪卷到了救生艇边,而我父亲成了那次海难唯一的遇难者。”
“那艘船成了他的棺材。讽刺的是,这个被玛利亚抛弃的男人,至死都守着他的‘玛利亚号’。”
“现在每次回到滨海布洛涅,我都要去码头看看。那里的小孩们还在踢着易拉罐,就像当年的我一样。只是现在他们追逐足球时,球衣上印着我的名字和号码。”
杜鲁克放下钢笔,沉默了片刻。
他摘下眼镜擦了擦,重新戴上后询问:“这个故事。你愿意让它见报吗?”
罗伊点点头。
杜鲁克轻声问道:“你父亲留给你最宝贵的财富,是这种牺牲精神吗?”